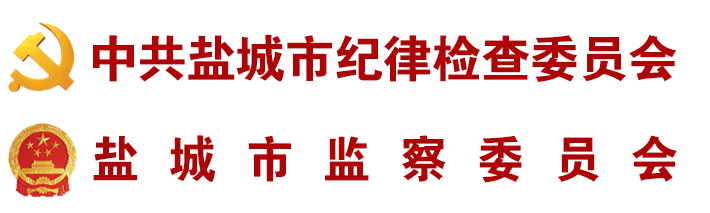贿赂不应仅作财产性解释
贿赂不应仅作财产性解释
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的不法交易,是通过“贿赂”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而“贿赂”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尽管古今中外各国立法对“贿赂”范围的规定各有不同,专家学者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我以为,它的性质依然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及能否成为交易的对象。因为只有能够满足需要的利益,才能促使掌握权力的官员不惜以出卖公共权力和利益去进行不法交换。
在实际生活中,满足需要的利益范围十分广泛(这是由人的各种需求决定的),表现形式又极其多样,这就形成了“贿赂”范围的广泛性。而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其实也并非仅指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而是泛指权力与利益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国家对“贿赂”的范围解释得较为宽泛,认为可以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任何其他利益,并非没有道理。当然,法律上对受贿、行贿犯罪的界定,一要考虑国家、社会利益的总体需要,二则必须注重其司法上的可能性、精确性。否则,再好、再理想的法律设计和理论构想,都难以在实践中获得实现,到时候极可能背负“立法虚设”、“打击不力”的评价,徒增社会不满,得不偿失。所以,对“贿赂”范围不作任何限制并不科学,必然会受到来自于司法操作层面上的种种限制或者变通。对待性贿赂,如今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国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律上没有对“贿赂”内容作出界定,但1985年7月“两高”则将“贿赂”的内容解释为“财物”一种形式。之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补充规定》,对此予以确认并规定对于犯受贿罪的,应当根据受贿所得的财物数量(数额)及情节,依照有关贪污罪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贿赂”内容中的“财产”属性,使国家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呈现出内容单一化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与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贿赂类型不相切合。
1997年修订的刑法仍然沿用以往的立法规范,将“贿赂”的内容确定为“财物”,使贿赂犯罪在法律上更像一般的财产犯罪,而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事实上又大大高于盗窃、诈骗、敲诈等罪行。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刚性”规定,使司法机关依据贿赂犯罪形式的多样化而对“贿赂”范围作重新解释的可能性近乎零,一定程度上更限制了对这类犯罪行为的处罚。
如今,社会上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形式、内容千变万化,不仅有财物交易、财产性利益交易,还有非物质性利益和需要(比如“性”、“色”)的交易。“性贿赂”作为其中的一种形式,可以起到财物贿赂方式难以达到的持续、重复等效果,对官员的腐蚀也可谓是“全方位”的。
我国刑法要真正起到对抗贿赂犯罪蔓延、扩大之势,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必须走“以动制动”之路。从全面、有效惩治贿赂犯罪的实际考虑,我们确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法律规范,不能固守“财物”一种形态,应当与时俱进的扩充受贿、行贿犯罪构成中“贿赂”的内容。
最为理想的方式是在法律上恢复1979年刑法典的内容,将收受、给予“财物”,统一改为接受、提供“贿赂”,再由最高司法机关对贿赂的内容根据实际状况和惩治需要作出解释,逐步将其解释为财物、能够予以计量的各种财产性利益及非物质性利益。同时,考虑到财物和财产性利益是贿赂犯罪的主要形式,也是司法惩处的重心,现行立法模式仍然可予以保留。由于非物质性贿赂方式(比如性贿赂等)情节各异,实际界定比较困难,为了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应当对它作单独、特别的规定或解释,可以先行将规范列举的情节较为严重的行为纳入定罪范围。这样处理,既符合刑事法律手段介入非法行为的刑事政策思想,体现慎刑主义,也有利于各类社会调节手段的协同配合,符合实际的有效惩治各类严重贿赂犯罪,积极回应中央近期提出的全面反腐败要求和民众对于官员廉洁的热切关注与期待。
来源:《法制日报》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