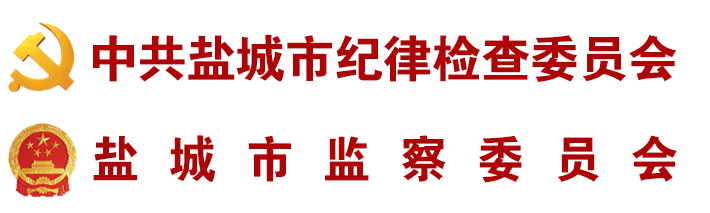女织
古人的生活图景,可一语概之:男耕女织。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乘机杼。”(孟郊《织妇辞》)
田夫蚕妾、牛郎织女,乃最典型的人生单元,亦是最完美的衣食组合和温饱设计,堪称天命。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
华夏先民的栖息史,五千年的村野炊烟,就这么飘飘袅袅,在“锄禾日当午”的挥汗和“唧唧复唧唧”的织声中,走到了21世纪。
恐怕谁也没想到,突然,它像滴空了水的漏钟一样,停了。
这个朴素的生活方程、貌似永恒的家务公式,其逻辑解散了,使命结束了。
城市,已彻底步入男不耕女不织的“大脱产”时代。乡村,男耕虽然依旧,女织却寥寥。当然,这是生产力飞跃和社会大分工之果,无可厚非。
我想说说“女织”,从人生美学的角度。
对“女织”的蒸发,我略感惋惜。我指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女织”,我看重的是“织”的情感承载和性别审美。抛开古人,说个我们熟悉的情景吧——
当一位女性在为恋人、丈夫、孩子织一件毛衣、围巾或袜子时,她用手指和棒针、用密密匝匝的经纬和几个月的凝神——所完成的仅仅是一件物吗?
当然不,这更像一场无声的抒情。她用温婉和柔韧,用细腻和漫长,用遐想和劳累,实现了一桩唯女性才能实现的心愿。每一针、每一环,都是一记笔画、一个字眼,她把所有心思都织了进去,融入这件最贴身的东西里去了。
这比甜言蜜语要贵重,比珠宝首饰要贵重。
为此,她的手可能会磨出茧泡,但她不在乎,心是甜的。
记得我年少时,几乎所有中国女人的怀里都有一团毛线,须臾不离,像抱着婴儿。即便在我的青春时代,大部分女人也如此。那会儿,机器造的羊毛衫已铺天盖地,但她们仍不放弃这项事业。当时杂志也纷纷为她们开辟了“针织”版,印象中的《八小时之外》《黄金时代》等,每期都有大量插页和彩图。
那个时代的女人,都会留下一枚标志:食指的上部略显糙厚。
她们是美丽而聪慧、多情而勤奋的女人。她们懂得“织”的元素和成分,懂得“亲手”的含义和象征,懂得用“缓慢”“琐碎”“麻烦”“辛苦”构造一件贴身之物意味着什么。她们享受这个过程,温暖别人,也感动自己。
所以,多数时候,“男耕女织”一词,让我想起的并非是劳动分工,而是“相濡以沫”“其乐融融”“琴瑟相伴”之类的伴侣之美。除了生育,“织”堪称古代女子最大的事业,是社会事业、生计事业,也是婚姻事业、感情事业。
“织”的背后,你总能看到那个字:情。无论春染梢头的豆蔻、贤妻良母的人妇,还是离愁黯伤的痴女,手中都有一情感道具:飞梭、织机或绣针。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调梭辍寒夜,鸣机罢秋日。良人在万里,谁与共成匹。”而《孔雀东南飞》中,有这样一段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是一个普通少女的成长简历和才艺档案。蚕、织、裁、缝、绣——几千年里,是每个女子的技能必修课。即便家境再优渥,也顶多是减去桑蚕纺工之累,纤绣之灵则不可少,换言之,即削弱体力劳动的成分、增加脑力劳动的含量。
我不以为此乃封建糟粕或性别压迫,相反,我觉得这是人生美学,乃女性的主动选择和天赋所赐,乃女性文化的灵魂和最闪光处。
织的是衣,纳的是袜,绣的是巾,可浸的是情,是意,是对生活的憧憬和幸福感。密密麻麻的线脚、纤巧灵盈的游走,织就的是女子的美丽和美德。
我一直觉得,女子一生中总该织点什么,否则有遗憾。
不为别的,就因她是妻子、是母亲,一个男人、一个孩子,身上若无一件由家中女性亲手完成的织物,至少逊了一份温馨。对敏感的体质来说,灵魂会略觉微凉罢。
有一个关于母织的当代故事,曾让我泪流满面。
也成了我作此文的动因之一。
这是2006年的一则新闻,题目是:《骨癌妈妈去世前为儿子织好25岁前所有毛裤》。
吉林白山一位家境贫寒、以烙煎饼为生的母亲,得知自己患绝症后,15个月里与死神赛跑,终于为9岁儿子织完了他25岁前需要的所有毛裤。
看着那幅照片,一个小小的孩子守着妈妈的遗像,床上一排排长短不一的毛裤,我流泪了。
也许,这位母亲想的是,等儿子25岁时,就能穿上另一个女人织的衣物了吧?(王开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