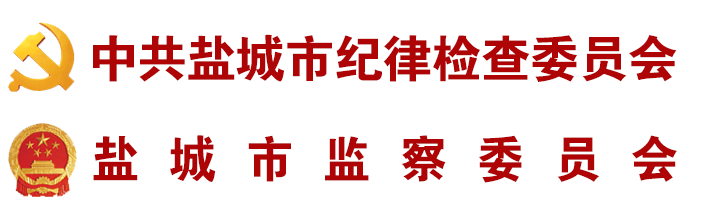拍蝇打蚊
昨夜蚊蝇入帐,肆意搅眠。几度举掌击拍,无奈蚊蝇窜逃迅疾,终未得手,由之任由去来,几至夙夜未眠。凌晨,见蚊帐边角黏附三颗米粒大褐色星点,近瞧,尽是“饱醉醺醺”的大肚蚊子。于是,平举双手,无需急速,凑前合掌,即见掌中“血迹斑斑”、“惨不忍睹”。转视蚊帐另一边角,见一苍蝇欣欣然优哉游哉,闭封蚊帐缝隙,取一蝇拍跟踪追击,苍蝇无处窜逃,应声掉落,一命呜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若非昨夜入帐搅眠,侵我睡乡,茹我肌血,亦不至于下手不留情,送尔等顷刻归西。
于是想到“四害”。“四害”之恶,早成共愤。国家早于1958年2月12日就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麻雀”被平反,由“臭虫”代替;再后来,“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如今“四害”所指乃为苍蝇、蚊子、老鼠和蟑螂。麻雀曾位列“四害”黑名单,有些冤!虽说它们喜欢糟蹋谷物,造成人类财产损失,可毕竟也有帮人类捉谷物害虫之功,且不至于给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直接伤害。其他“诸害”则不然,要么惯常与肮脏龌龊为伍而给人类带来疾病,要么暗地里专事损人利己的蝇营狗苟勾当,着实让人生厌。愚以为,蚊蝇尤甚。
据说,蚊子的平均寿命不长,雌性为3-100天,雄性为10-20天。它们的食物一般是花蜜和植物汁液,雌蚊却需要叮咬动物以吸食血液来促进内卵的成熟。原来“夜来侵帐”者竟是雌蚊!激愤于雌蚊胆大包天的同时,不觉对雄蚊的“安分守己”抱以一丝肯定和赞赏。而多行不义必自毙,雌蚊“饕餮盛宴”之后短寿赴黄泉,自是咎由自取、罪责难逃,即便“吸食血液”固有其“促进内卵成熟”之繁衍生息所需,可终究不是吸食人血的正当性理由——雌蚊千不该、万不该自不量力、不计后果地在强大人类面前侥幸试胆。相对于吸食人血,雌蚊之恶更大者在于“高调扰眠”。鲁迅曾在《夏三虫》一文中这样写道:“跳蚤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无怪乎鲁迅就此表示,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于蚊虫跳蚤孰爱?”我一定毫不迟疑,答曰“爱跳蚤!”这理由很简单,就因为跳蚤是咬而不嚷的。看得出,鲁迅爱跳蚤厌蚊子,并非真意怀之,而是“二害相权取其轻”的情非得已。因为,“闷声吸血”也好,“高调吸血”也罢,其行为结果没有两样,都是以暗地行偷、损人利己为行为旨归。至于苍蝇,真正令人厌恶的是其龌龊与肮脏,它们忽而在厕所里吸吮,忽而在垃圾堆上寻觅,忽而在臭水沟中穿梭,忽而又光顾人的饭菜里……以至于一旦饭菜里有苍蝇涉足,多数人都会选择将整碗饭菜倒掉。苍蝇嗜喜污浊,惯常与肮脏为伍,它们是人类罹患疾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蚊子吸食人血,假若仅为人血数量上的物理性递减而无他害,也就作罢,权且视其为“普度众生”的博爱犒劳,亦可满足人类的默默奉献之善念。然而,事实上远非如此。其一,蚊子吸食人血之前务必与人类“亲情零距离”,飞临人体时翅膀高频挥动由所发出的嗡嗡声(即鲁迅所谓“发一篇大议论”),必使夜眠者难以酣睡,浅睡眠者或神经衰弱者尤受其害;其二,蚊子吸食人血,极易在人际间传播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乃至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其三,为预防蚊子入帐,人类发明了蚊香、蚊帐、纱窗、纱门等诸多防蚊物品,多量化制造和使用这些物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必然促成人类钱财的大量流失。苍蝇虽然不吸食人血,其害跟蚊子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一文中写道:“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欧阳修则在《憎苍蝇赋》这样形容苍蝇:“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苍蝇“间白黑”、“谗巧”、“逐气寻香,无处不到”固然可恨,最可恨者,则莫过于挥之难去的骚扰纠缠。譬如夜间,人们睡意正浓,苍蝇入帐侵扰,时而在耳际边嘤嘤绕绕,时而停落脸面眉梢,黑暗中举手拍打不着,亮灯起坐拍蝇不是,任其肆意搅眠也不是,着实令人烦躁乃至几近崩溃。明人谢肇淛就曾斥骂苍蝇比蚊子、毒蛇、蝎子更恶劣,终日营营,搅扰起人来太过厉害,“比之馋人,不亦宜乎!”
“四害”之害,蚊蝇尤甚,为剔除蚊蝇纠缠扑面之害,保障人体身心健康、构筑和谐安居环境,“拍蝇打蚊”势在必行。
(张少华 作者单位:福建省平和县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