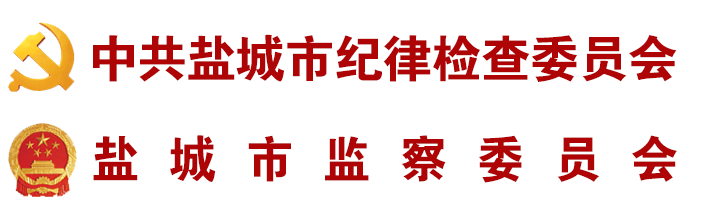踏 空
我身上有几块疤痕,是踏空摔伤所致的。
我额头的伤疤,缝过十二针。我妈说,吓死她了。她说,我从老高的炕沿往前扑,一脚踏空头落地,栽在三角石上,头破血流,人没气了。她往血口抹了把灶灰,摸着我身上有丝温热,赶紧抱起往医院跑。
医院在十里远的县城,在没车的泥路上,母亲抱着我跑。我的伤口仍在流血,她磨破的脚也在流血和钻心地痛。一路奔跑的母亲,豁出命来往医院赶。跑到医院时,母亲看我额头翻绽的伤口不再流血,身上冰凉上涌,就地软瘫了。抢救的医生对我发抖的母亲说,人还活着,有救。她听医生说有救,身上又有了劲,眼泪却止不住了。
母亲抱着我跑了那么远的路,哪来的力气,我想象不出来;母亲如在路上稍有停顿,我就没命了。
有几次母亲摸着我额头的伤疤,痛楚地述说那次的踏空。这个伤疤,自从被唤醒,每当有东西触及到它,风雨雪刺激到它,甚至镜子照到它的时候,会有隐约的痛感。伤痕留在额头不愿走,照镜子会看到它,梳头会碰到它,不经意会摸到它,母亲常会端详它。我知道,最在意的是母亲,母亲端详它的那眼神,仍有揪她心的感觉。她常说起我踏空的事,是在不停提醒我,抬脚有危险,走路得长“眼”,踏空会要命。
寒冬的冰酷似石般结实,我却踏空了。幸亏姐眼疾手快,否则我就不在人世了。姐说,那时我七岁,河沟刚结冰,冰下是急水,我要下沟滑冰。她拉不住,我踏破冰便落水了。沟里全是冰,她破冰费尽周折找到了我,待把我从冰沟拉出来时,我已满肚子冰水,人快没气了。活过来的我,一病数天又烧又拉,人瘦成了脱水的瓜条。她为我又累又惊生了病,也一病数天不起,人瘦得脱了相。我问姐,你是怎么把我从冰沟找到的?姐说,砸冰找的,你命大,差点找不到了。
每当提起这事,姐总说踏空会要命,脚下可得小心。我说那么厚的冰,怎么会踏破呢?姐说那是“骗”人的冰,踏上就破。姐的话对,河沟上的冰会“骗”人。河上的冰看是实的,冰下却是空的,总有人踏空落水或送命的。
踏空甚至会发生在好端端的平地上。
我在宽阔而平坦的田埂上信马由缰地走路,压根儿没料到会在这光溜的道上踏空,可我的脚却踏空了。这踏空是塌陷式的下沉,一脚下落,踩到了极软的东西,随着惊叫,数条硕鼠惊恐上蹿。
是我踏到了鼠穴。这平而硬的田埂,怎么会有鼠穴呢?原来路是被硕鼠掏空了的,掏成了大空洞。可我纳闷,这田埂每天走人,为何偏让我给踏空了?我想不明白。
踏空之祸藏在脚下。每当自己三心二意走路时,往往就会踏空。踏空过马路,有人把稻草盖在坑上,把我的脚崴了;踏空过台阶,我把脚踏到了底层,摔伤了一条腿;踏空过木板,那是实里藏虚和虫子咬空的硬木板,造成了皮伤和惊吓;踏空过山石,我从山坡溜了下去,差点摔成一堆肉泥。至于小的踏空,已不计其数了。因而,抬腿就怕踏空。想起踏空,心就颤抖。
人一生的路有多长,通常是脚“说”了算。因为,没有比脚更远的路。踏空,往往是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或者粗心大意所致。其实,只要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走路,无论山路还是平地,都会避免踏空;即便是偶有闪失,也会毅然决然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向前走。(宁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