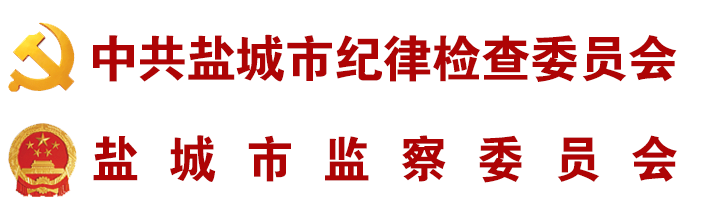民主执政与群众路线: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基本逻辑
民主执政与群众路线:
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基本逻辑
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基本逻辑
宋 霁
近年来,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学术界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给予高度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试图从中寻找到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原因,进而总结归纳出有益于当前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新四军及其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为全面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在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教育的经验和制度,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治党、治国和治军的优秀干部,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历史地看,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廉洁政权的建立。我们认为,民主执政和群众路线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两条基线。前者从制度层面,后者从作风层面共同确保了廉洁政权的诞生。
一、民主执政:廉洁政权建设的制度保障
中共在华中地区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打下了组织基础。中共成立之初,江浙一带就有了党组织,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了多次农民暴动,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撤退后,皖西北等地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仍旧坚持斗争。然而,到抗战前夕,华中地区大多数秘密组织在严酷的环境中遭到破坏,除游击队外,仅留下隐藏在大别山、桐柏山等地游击区、边沿区或个别大城市的河南省工委、鄂豫边特委、徐州特委、上海江苏省委的部分组织和文化界外围组织。
抗战爆发后,中共明确了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在贯彻统一战线总体政策的前提下,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根据地武装斗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华中各地区积极恢复党组织,与新四军一起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各级组织按“三三制”原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县、区、乡各级政府,并建立群众团体和自卫队。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以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并依照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公布财政、贸易、税收、征收公粮等法令、条令;推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等政策;动员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肃清汉奸和救灾优抚工作;在县、区、乡设立三级武装力量。“经过各方面努力,到抗战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拥有淮北、淮南、皖江、苏北、苏浙(苏南、浙西)、浙东、鄂豫皖湘赣等八个行政区、四十座县城的广大解放区。”
与日伪势力的清剿、掠夺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占领、反共政策不同,中共在根据地的执政建设是立足中国农村的现实,从解决农民根本需要、建立民主政权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出发的,因而形成了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1)
在政权建设方面,出于对抗战全局和根据地所处现实背景的思考,中共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性。(2)在所有根据地无一例外地实行“三三制”,即中共党员在根据地政府和参议会里最多只占三分之一的职位。与国民党形成对比的是,“三三制”表明共产党愿意也有能力与革命的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并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3)
有研究认为,“三三制”合作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的。(4)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5)
参照“三三制”的基本原则,为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1942年,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均、黄桥的朱履先等,共产党员在这些组织中均只占三分之一。至当年年底,苏中地区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和3O 个区成立了符合“三三制”原则的参议会。
从现实功用上来看,“三三制”在敌后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所遵循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方针与游击战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它的实行不仅将地方势力广泛地吸纳到根据地政权中来,创造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而且也大大增加了根据地政府的合法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决定权常常是由所有群体共同作出的”;可以说,“三三制”帮助中共在根据地建立起稳定的政府。(6)
在制定政权组织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共还在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7) “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在削减开支和裁撤冗员,而在于对政府的结构、构成和观念方面的改变。下层政府,尤其是乡政府得到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得到了加强,地方关系网逐步突破。这些举措是由党和政府联合发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铺平了道路。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党对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安排,增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使政府的目标更接近人民,更能满足当地的需要。(8)
在土地与经济建设方面,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封锁的不断加强,以及日军清剿行动的有增无减,根据地的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共开始改变关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土地政策决议”,直接引发了减租和打击地主的群众运动。但是,此时的土地政策已从中央苏区时期的激烈土地革命政策中吸取了教训,它将以减租为外衣的土地革命与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结合起来,以温和的、阶级合作的调子来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此后,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生产仗”与抗战成为同等重要的问题。减租是解放农民发展经济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投身于减租运动的农民收获更多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精神上的鼓舞,激发了“生产热情”,为根据地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9)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坚持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在每一个乡村都设有党支部,在部队的连队中也都设有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组织如同末梢神经一样,可以迅速执行中央的指示、任务,可以迅速地把农村的力量整合起来,凝聚起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正是凭借在农村基层的出色组织工作,中共才得以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打下扎实的物质与人力基础,才能够打破日伪顽三方势力对根据地实施的经济封锁与破坏,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推动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在执政方式建设方面,中共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0)反对官僚作风,坚持军民互助,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各级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必须要到部队、到基层一线去领导和参与对敌斗争,确保党和政府的所有组织在战争环境下继续坚持运作,发挥作用,这些对最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策略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共的这种组织形式和执政模式很好地适应了抗战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党员在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将大家拧成一股劲,增强了抗日力量。这些举措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热情,有效保护和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反观国民党,其在华中主要推行纯粹的军事占领以达反共目的,根本不注重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以组织建设为例,国民党党部仅设在县一级,这就意味着其执行力无法贯彻到乡、村一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看不起”普通百姓的政治取向。事实上,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恰恰就在广大农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分别提出军队建设和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褚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和乡村建设等提案,尽管这些提案都在大会上获得通过,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把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意见当回事。如此没有根基的政权如何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何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此时,中共的根系已通过有效的执政建设,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土壤深处,正从中不断汲取养分,积蓄力量。
二、群众路线:廉洁政权建设的作风保证
与国民党“抛弃”人民大众不同,(11)中共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在实践中不断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历史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三三制”,还是“减租减息”运动,无论是基层组织建设,还是作风建设,贯穿在这一系列制度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这也为廉洁政权的建设提供了作风保证。
从理论上讲,群众路线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两方面构成。前者是群众路线的价值归宿和理论起点,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际运用,即从“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公式转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的领导和工作方式。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早在中共“二大”就得到了体现,当时中共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12)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这年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13)
此后,中央苏区的严酷现实、残酷的战争形势和农村有限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党在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坚定了依靠群众的思想。(14)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实践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15)正是在这些具体实践中,“群众路线”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农民的直接利益逐渐发展出来。这一执政理念和思路一直贯穿始终,并在敌后根据地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16)
在准确认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和为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基础上,抗日敌后根据地建设时期的中共,更加注重在权力结构和执政模式两方面来贯彻“群众路线”。(17)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外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周恩来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深入群众。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谓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我们要道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 (18)二是对党内调整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有研究认为:“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为了指导建立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正确’关系。它是马列主义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19)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被缩小了,有效应对了中国农民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缺陷,(20)同时也发挥了基层组织和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21)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政治觉悟的领导层与当地社区中那些目不识丁、远离政治的大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疑难,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地的经验及相应的理论,将大众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接着,又将这些总结出来的意见拿回到大众中去进行实践和检验,及时发现新问题。最后取得多数人的同意,作出决议,指导实践。这种政治方法使全体民众都积极投身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这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广大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克服他们的政治沉默、对变革的疑虑、对现代技术及组织效能的无知、对外界的无知、对政府的恐惧,以及他们狭隘的家庭宗族观念和短视的经济观点。” (22)
从执政模式的角度来讲,也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作风建设要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3)二是革命运动的方法是要以动员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革命的进程和民主政权的建设。1942年2月,华中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就明确提出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以“精兵简政”运动为例,“对动员政治的活力所作的概括,是对行政机关的凝固化和官僚化倾向的直接挑战。毛泽东所向往的是一种运动型的政治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在这种运动型政治中,群众和干部集中力量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旗帜鲜明地反对行政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狭隘的专业化。在不断受到日军侵扰的根据地,这种政治风格对于快速进行军事和政治动员的游击战略至关重要。”(24)
可以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共成功开辟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西方理论中关于革命一般都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及其周边的理论假说,成为中共对世界革命的创造性贡献之一。而群众路线的方法和理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明确使用过“群众路线”的概念。(25)群众参与和民主监督亦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两大法宝。
(作者简介:宋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教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王绍光从“政体”和“政道”的辨析中,指出,“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于‘要求’,而以回应性为特征民主着眼点是最广大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要求”是指人们想要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所必要的那些东西,是被创造、制造出来的,而“需求”主要是指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的必须的东西。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人间正道》,第190页。
(2) 对“三三制”的理解必须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中去认识。在一些根据地中,党的组织力量尚未巩固,地方上的地主、士绅和商人阶层势力还较强,采取激进的没收财产、重新分配财产等手段并不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同时,这些地区尚不具备正规选举的基本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和逐步加强党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因为“三三制”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最重要的是,它利用党组织的行政能力和领导技巧,来赢得和扩大各界的支持。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7页。
(4)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6)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7页。
(7) “精兵简政”过程中,原先的纵向行政结构受到了批评和改正,双重领导的新体系成为主导,党的领导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功能得到增强。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央所写的一个决议中,曾对双层领导作过经典性的说明:“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结合的一种形式。”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901页。
(8)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08页。
(9)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21-222、225页。
(10) 毛泽东特别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提倡“下马观花”,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如何能在调查研究中听到群众的真话,他认为:“主要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1) 1920年代初,国民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始终没有体现出一个“群众党”、“人民党”的定位。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整个来说,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即便是在国民党一大确立“三大政策”之后,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人民群众仍然无法进入国民党的视野,绝大部分的群众工作和工人运动都是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来具体负责运作。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呈现出国民党做上层工作,共产党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二、三、四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版。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3) 施光耀:《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4期,第145-146页。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第16-17页。
(14) 毛泽东和党的早期领袖们也反复强调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成为党的两大任务。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土地革命策略制定方面,我们党多次强调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关心并组织好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9、136、138页。
(15) 曹春荣:《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9月号,第12-15页。
(16) 新四军用枪杆子在华中敌后先后建立起来的苏南、淮南、苏中、鄂豫边、淮北、苏北、皖江、浙东等抗日根据地,可以说全部是在农村,是依靠农民群众支持而建立的,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抗日和革命的阵地,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本质上是一致的。马洪武:《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二十五年》,《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17) 从宏观视角来看,“群众路线”解决了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合法性问题——权力的人民性。这是进一步探讨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权力结构和执政模式的基本前提。
(1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9) 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诠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0) 1940年代,中国的农村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农村社会的相对贫困、落后、闭塞以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场变动中面临着重构的要求。要实现秩序的重构,其关键在于重构后的治理结构要同时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共的成功就在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村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努力作为都能在农民中产生强大的共鸣。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直选”制度为例,农民的兴趣和实际参与率并不高。面对现实,中共及时调整策略,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行政网络,主动寻求行政资源的介入,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引导处于观望和怀疑中的农民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通过整顿党的作风来转变工作方式,推进治理的有效性;通过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来赢得民心,获得合法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乡村权威结构和政治秩序的重建。
(21)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59-260页。
(22) 杰克•格雷等:《危急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纽约,1968年,第49-50页。格雷还指出,这种方法也用于民族团结和劳动纪律的加强以及对官僚腐败与僵化的防范。转引自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59页。
(23) 参见注21。
(24)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10页。
(25)瘳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有国外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参见Edward Hammond, Marxism and the Mass Line, Modern China, Vol.4, No.1, 1978.
(1) 王绍光从“政体”和“政道”的辨析中,指出,“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于‘要求’,而以回应性为特征民主着眼点是最广大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要求”是指人们想要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所必要的那些东西,是被创造、制造出来的,而“需求”主要是指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的必须的东西。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人间正道》,第190页。
(2) 对“三三制”的理解必须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中去认识。在一些根据地中,党的组织力量尚未巩固,地方上的地主、士绅和商人阶层势力还较强,采取激进的没收财产、重新分配财产等手段并不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同时,这些地区尚不具备正规选举的基本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和逐步加强党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因为“三三制”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最重要的是,它利用党组织的行政能力和领导技巧,来赢得和扩大各界的支持。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7页。
(4)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6)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67页。
(7) “精兵简政”过程中,原先的纵向行政结构受到了批评和改正,双重领导的新体系成为主导,党的领导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功能得到增强。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央所写的一个决议中,曾对双层领导作过经典性的说明:“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结合的一种形式。”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901页。
(8)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08页。
(9)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21-222、225页。
(10) 毛泽东特别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提倡“下马观花”,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如何能在调查研究中听到群众的真话,他认为:“主要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1) 1920年代初,国民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始终没有体现出一个“群众党”、“人民党”的定位。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整个来说,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即便是在国民党一大确立“三大政策”之后,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人民群众仍然无法进入国民党的视野,绝大部分的群众工作和工人运动都是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来具体负责运作。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呈现出国民党做上层工作,共产党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二、三、四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版。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3) 施光耀:《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4期,第145-146页。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第16-17页。
(14) 毛泽东和党的早期领袖们也反复强调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成为党的两大任务。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土地革命策略制定方面,我们党多次强调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关心并组织好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9、136、138页。
(15) 曹春荣:《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9月号,第12-15页。
(16) 新四军用枪杆子在华中敌后先后建立起来的苏南、淮南、苏中、鄂豫边、淮北、苏北、皖江、浙东等抗日根据地,可以说全部是在农村,是依靠农民群众支持而建立的,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抗日和革命的阵地,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本质上是一致的。马洪武:《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二十五年》,《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17) 从宏观视角来看,“群众路线”解决了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合法性问题——权力的人民性。这是进一步探讨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权力结构和执政模式的基本前提。
(1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9) 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诠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0) 1940年代,中国的农村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农村社会的相对贫困、落后、闭塞以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场变动中面临着重构的要求。要实现秩序的重构,其关键在于重构后的治理结构要同时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共的成功就在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村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努力作为都能在农民中产生强大的共鸣。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直选”制度为例,农民的兴趣和实际参与率并不高。面对现实,中共及时调整策略,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行政网络,主动寻求行政资源的介入,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引导处于观望和怀疑中的农民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通过整顿党的作风来转变工作方式,推进治理的有效性;通过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来赢得民心,获得合法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乡村权威结构和政治秩序的重建。
(21) 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59-260页。
(22) 杰克•格雷等:《危急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纽约,1968年,第49-50页。格雷还指出,这种方法也用于民族团结和劳动纪律的加强以及对官僚腐败与僵化的防范。转引自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59页。
(23) 参见注21。
(24)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10页。
(25)瘳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有国外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参见Edward Hammond, Marxism and the Mass Line, Modern China, Vol.4, No.1,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