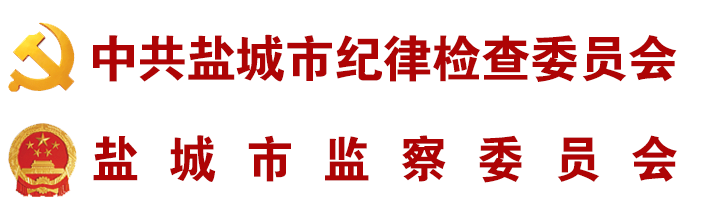村庄的痛和爱
村庄的痛和爱
我又去了一趟这个名叫洪水庄的村庄。
两条山脉平行延展时,好似商量好的,在这里同时拐弯儿,恰如两根粗粝的纠结在一起的胳臂肘子间留出的薄薄的一条缝隙。风从这里尖叫着挤过去,洪水从这里喧嚣着挤过去。昨天挤过去的风今天又来了,一年四季,这里便成了一条风路。以前在每年春夏秋三季隔三间二都要从这里挤过去一回的洪水,如今只有在盛夏季节偶尔光顾一次,除了把残留在洪水沟的数量极其菲薄的枯枝败叶和羊粪豆儿清洗干净外,在情绪比较昂扬时,还会迅捷地漫上两边扁担宽的条田里,将各种本来就显得萎靡的庄稼连根卷起,哂笑着,逍遥远去。
不知在何年何月,有那么一个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一对男女,也可能是兄弟俩,或母女俩,抑或是父子俩、姊妹俩——都有可能的——看见风从这里挤过去了,洪水挤过去了,他们本来也是打算从这里挤过去,像风或洪水那样,走向远方的。但,他们在往过挤时,也许是累了,也许觉得这地方还不错,就在这里的黄土峭壁上凿出几孔简易的窑洞,落脚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峭壁上居然被凿出了上百孔窑洞,数百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以家的形式分住在属于自己的窑洞里。
一个村庄俨然诞生了。诞生了的村庄俨然一个村庄。诞生了的生命就有理由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活下去。诞生了的村庄当然有理由,也有责任,以村庄的姿态延续下去。
村庄名叫洪水庄。名字不知出自谁的智慧,想当然地说,当年以洪水命名村庄,到底是实至名归的,这有那一条贯穿全村的深刻的洪水沟作证。同样可以想当然地说,洪水是这个村庄成为村庄的前提。因为村里逼仄的空地上残留着大大小小十多处涝池,每个涝池都有岔口连接洪水沟。涝池的作用是,将洪水引入、积攒下来,作为旱季的生活用水。如今,大多涝池终年无水可蓄,皲裂的干泥片儿象征着这只是一个曾经的村庄。
国家在千里之外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绿洲,洪水庄被列为首批移民村庄。政府来人三番五次动员搬迁,可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洪水庄。多少年了,村民们无数次望着不下雨的天,一遍遍划拉着不长庄稼不生草木的土地,小声咒骂着不通人情的天,甚至咒骂着瞎了眼睛的祖先,恨不能凭空生了翅膀,携家带口飞向冥冥之中的肥田沃土,享受现世的幸福。可是,当真的生出了飞翔的翅膀后,他们却不愿飞了。一夜间,故土是那样的令人留恋,这里的山山水水仿佛自身的血脉经络,牵扯到某个部位,引发的都是深刻的痛、由衷的爱。公家人懂得洪水庄人的心理,他们说,前往的地方,没有别的居民,洪水庄的建制不会被打乱,甚至洪水庄的村名都可以保留。那里平原广阔,灌渠纵横,国家出资建造的房屋宽敞明亮,居住条件比城里人都要好。某个心眼较活的村民心眼动了,也只是动了一下,随即心口那里便是一阵惊悸。离开村庄无异于婴儿离开父母,世间一切景致带来的无一例外都是迷茫和恐惧。
一些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心眼活了,真的活了,他们能看得懂国家提供的地图。迁往的地方仍然是地球上的一片土地,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本省。一个群体在面临同样的抉择时,所有人在某个特定时刻都处在无主张状态。这时,只要有一个人作出了决定,哪怕这是最糟糕的决定,所有人立即都会心明眼亮,把它当成最佳的、唯一的决定。
离开村庄的时刻无可阻挡地到来了,此时,哪怕只是一束茅草都那样宝贵。他们把一切能拿走的,统统装上国家提供的大卡车。牛驴猪羊鸡,坛坛罐罐,一样不能少。只可惜,土地拿不走,哪怕只有扁担宽的、十种九不收的土地。小孩欢叫着爬上从未坐过的卡车,他们还不懂得离乡背井的悲伤。大人一步三回头,女人和老人哭哭啼啼,互相劝解着,被劝解的人哭,劝解别人的人也在哭。终于,一辆辆卡车开动了,洪水庄在卡车的轰鸣中陷于沉寂。
那一天,我去了洪水庄,他们要迁往的地方此前我已去过了。在我看来,无论以什么样的眼睛、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世界,洪水庄人都应该算是由地狱步入了天堂。
可是几年后,我听说,稍有点年纪的人大多又返回了洪水庄。这是我再度来洪水庄的原因。我想探究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天堂重返地狱。我问了许多人,许多人默然无语,许多人言语嗫嚅,而神情既淡然又坚定。我问是那里生活苦吗,他们说,不苦,比这里好多了;我问是受本地人欺负吗,他们说,那里没有本地人,一个村子都是洪水庄人。我的理解能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我不知道到底该问什么,该怎样发问。沉默许久,一个原来当过村支书的老者也许看出了我的尴尬,先前他是应付过一些场面的。他有些难为情地说,住在那里,主要是心里不踏实。在田里干活好像脚下踩的是浮云,看见满仓的粮食老觉得是梦境,吃完饭,肚子倒是饱了,可嘴里一点味道都没尝出来,宽敞漂亮的房子老觉得是画上的,收工回家忍不住要伸手摸摸墙壁,看是不是真的,半夜醒来,也要摸一摸墙壁,害怕是做梦睡在野地里呢。说完,他呆望着眼前的秃山,神情一片空茫,继而脸生激愤之色。他说,我不是说你,没当过农民的人不理解农民嘛!有些人说我们是愚民,谁不知道国家是为我们好,我们没有文化,难道连饭香屁臭都闻不出来?不是那回事嘛!在哪里长大的人,一辈子都是哪里的人。等那些生在灌区的孩子长大了,你去问问他们还愿不愿回到洪水庄?父母把他们生在那里,那里当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在这里,这里当然就是我们的家。自己的家自己不爱让谁去爱?自己的爹妈生得丑,难道要找生得漂亮的当爹妈?
我是怀着满肚子惆怅离开洪水庄的。出村口时,我回头向村庄盯视了好大一会儿,村庄比先前更破败了,人们在田间地头忙碌,可注定他们的忙碌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就在我要离开洪水庄时,我突然觉得,那些在无望的田地里忙碌的身影与那片天地是那样和谐,他们行走在山窝里的脚步是那样坚实,他们忧郁的眼神投射在那片土地上时,显现出来的却是心安理得的淡定和从容。
此时,我似乎勘破了某些有关村庄的玄机,我似乎窥见了村庄对于生长于村庄的人所拥有的那种超越功利的意义。
从此,我便拒绝用功利的眼光去审视村庄。
两条山脉平行延展时,好似商量好的,在这里同时拐弯儿,恰如两根粗粝的纠结在一起的胳臂肘子间留出的薄薄的一条缝隙。风从这里尖叫着挤过去,洪水从这里喧嚣着挤过去。昨天挤过去的风今天又来了,一年四季,这里便成了一条风路。以前在每年春夏秋三季隔三间二都要从这里挤过去一回的洪水,如今只有在盛夏季节偶尔光顾一次,除了把残留在洪水沟的数量极其菲薄的枯枝败叶和羊粪豆儿清洗干净外,在情绪比较昂扬时,还会迅捷地漫上两边扁担宽的条田里,将各种本来就显得萎靡的庄稼连根卷起,哂笑着,逍遥远去。
不知在何年何月,有那么一个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一对男女,也可能是兄弟俩,或母女俩,抑或是父子俩、姊妹俩——都有可能的——看见风从这里挤过去了,洪水挤过去了,他们本来也是打算从这里挤过去,像风或洪水那样,走向远方的。但,他们在往过挤时,也许是累了,也许觉得这地方还不错,就在这里的黄土峭壁上凿出几孔简易的窑洞,落脚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峭壁上居然被凿出了上百孔窑洞,数百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以家的形式分住在属于自己的窑洞里。
一个村庄俨然诞生了。诞生了的村庄俨然一个村庄。诞生了的生命就有理由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活下去。诞生了的村庄当然有理由,也有责任,以村庄的姿态延续下去。
村庄名叫洪水庄。名字不知出自谁的智慧,想当然地说,当年以洪水命名村庄,到底是实至名归的,这有那一条贯穿全村的深刻的洪水沟作证。同样可以想当然地说,洪水是这个村庄成为村庄的前提。因为村里逼仄的空地上残留着大大小小十多处涝池,每个涝池都有岔口连接洪水沟。涝池的作用是,将洪水引入、积攒下来,作为旱季的生活用水。如今,大多涝池终年无水可蓄,皲裂的干泥片儿象征着这只是一个曾经的村庄。
国家在千里之外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绿洲,洪水庄被列为首批移民村庄。政府来人三番五次动员搬迁,可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洪水庄。多少年了,村民们无数次望着不下雨的天,一遍遍划拉着不长庄稼不生草木的土地,小声咒骂着不通人情的天,甚至咒骂着瞎了眼睛的祖先,恨不能凭空生了翅膀,携家带口飞向冥冥之中的肥田沃土,享受现世的幸福。可是,当真的生出了飞翔的翅膀后,他们却不愿飞了。一夜间,故土是那样的令人留恋,这里的山山水水仿佛自身的血脉经络,牵扯到某个部位,引发的都是深刻的痛、由衷的爱。公家人懂得洪水庄人的心理,他们说,前往的地方,没有别的居民,洪水庄的建制不会被打乱,甚至洪水庄的村名都可以保留。那里平原广阔,灌渠纵横,国家出资建造的房屋宽敞明亮,居住条件比城里人都要好。某个心眼较活的村民心眼动了,也只是动了一下,随即心口那里便是一阵惊悸。离开村庄无异于婴儿离开父母,世间一切景致带来的无一例外都是迷茫和恐惧。
一些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心眼活了,真的活了,他们能看得懂国家提供的地图。迁往的地方仍然是地球上的一片土地,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本省。一个群体在面临同样的抉择时,所有人在某个特定时刻都处在无主张状态。这时,只要有一个人作出了决定,哪怕这是最糟糕的决定,所有人立即都会心明眼亮,把它当成最佳的、唯一的决定。
离开村庄的时刻无可阻挡地到来了,此时,哪怕只是一束茅草都那样宝贵。他们把一切能拿走的,统统装上国家提供的大卡车。牛驴猪羊鸡,坛坛罐罐,一样不能少。只可惜,土地拿不走,哪怕只有扁担宽的、十种九不收的土地。小孩欢叫着爬上从未坐过的卡车,他们还不懂得离乡背井的悲伤。大人一步三回头,女人和老人哭哭啼啼,互相劝解着,被劝解的人哭,劝解别人的人也在哭。终于,一辆辆卡车开动了,洪水庄在卡车的轰鸣中陷于沉寂。
那一天,我去了洪水庄,他们要迁往的地方此前我已去过了。在我看来,无论以什么样的眼睛、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世界,洪水庄人都应该算是由地狱步入了天堂。
可是几年后,我听说,稍有点年纪的人大多又返回了洪水庄。这是我再度来洪水庄的原因。我想探究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天堂重返地狱。我问了许多人,许多人默然无语,许多人言语嗫嚅,而神情既淡然又坚定。我问是那里生活苦吗,他们说,不苦,比这里好多了;我问是受本地人欺负吗,他们说,那里没有本地人,一个村子都是洪水庄人。我的理解能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我不知道到底该问什么,该怎样发问。沉默许久,一个原来当过村支书的老者也许看出了我的尴尬,先前他是应付过一些场面的。他有些难为情地说,住在那里,主要是心里不踏实。在田里干活好像脚下踩的是浮云,看见满仓的粮食老觉得是梦境,吃完饭,肚子倒是饱了,可嘴里一点味道都没尝出来,宽敞漂亮的房子老觉得是画上的,收工回家忍不住要伸手摸摸墙壁,看是不是真的,半夜醒来,也要摸一摸墙壁,害怕是做梦睡在野地里呢。说完,他呆望着眼前的秃山,神情一片空茫,继而脸生激愤之色。他说,我不是说你,没当过农民的人不理解农民嘛!有些人说我们是愚民,谁不知道国家是为我们好,我们没有文化,难道连饭香屁臭都闻不出来?不是那回事嘛!在哪里长大的人,一辈子都是哪里的人。等那些生在灌区的孩子长大了,你去问问他们还愿不愿回到洪水庄?父母把他们生在那里,那里当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在这里,这里当然就是我们的家。自己的家自己不爱让谁去爱?自己的爹妈生得丑,难道要找生得漂亮的当爹妈?
我是怀着满肚子惆怅离开洪水庄的。出村口时,我回头向村庄盯视了好大一会儿,村庄比先前更破败了,人们在田间地头忙碌,可注定他们的忙碌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就在我要离开洪水庄时,我突然觉得,那些在无望的田地里忙碌的身影与那片天地是那样和谐,他们行走在山窝里的脚步是那样坚实,他们忧郁的眼神投射在那片土地上时,显现出来的却是心安理得的淡定和从容。
此时,我似乎勘破了某些有关村庄的玄机,我似乎窥见了村庄对于生长于村庄的人所拥有的那种超越功利的意义。
从此,我便拒绝用功利的眼光去审视村庄。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