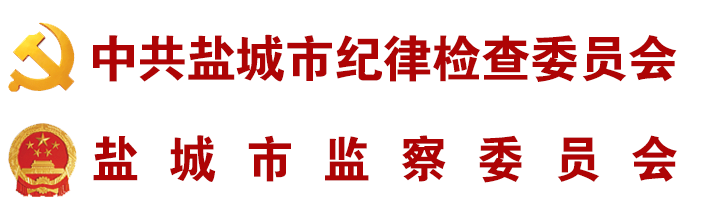忏悔
我在街上看见了马厂长。马厂长退下来三十多年了,人显得很老。他步履蹒跚着,拄着拐棍,走路颤颤巍巍。见到我,自是亲切。
我问候着马厂长。他却岔开我的话茬,问:“听说鲁刚住院了?他得了癌症?住院了?”
我告诉马厂长,我刚去医院看过鲁刚。
马厂长一声长叹:“多好的人啊!”接下来,马厂长说了一件事,他感到,对不起鲁刚!
马厂长说的这件事,我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要提拔一位副厂长。马厂长相中的是吴伟山,可吴伟山是中专文凭,不如大专文凭过硬。怎么给吴伟山增加点砝码呢?当时,鲁刚正领着人搞“双革”攻关的项目,而且,搞成了。马厂长想也没想,就把“双革”的成果张冠李戴,算到了吴伟山的头上。
其实,吴伟山只是“双革”小组的成员,图纸还是鲁刚亲自画的呢。吴伟山没吭气,鲁刚也没吭气。这件事就这么报上去了,吴伟山戴上了大红花,还真就提了副厂长。
“一想起这个事,我就心痛,我错了,对不起鲁刚!”马厂长喃喃自语。
“放心吧,回头我告诉鲁刚。”
马厂长蹒跚着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得摇了摇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说什么,都晚了!
鲁刚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是一头踏踏实实的老黄牛!
我很了解鲁刚,几十年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鲁刚除了是生产能手外,油画也十分了得,他的画作,在省市都获得过一等奖。退下来后,鲁刚成了老年大学的义务教员,风里来、雨里去地给学员上课。很不幸,这时候,他得了癌症。每次,我见到他在老年大学讲课,鼻子都酸酸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教室出来,到传达室坐了坐,我在传达室值班。他头上冒着汗,身上也流着汗,秋衣和秋裤都浸湿了!
他经常住院。好在,我家离职工医院不远,我经常去看他。我考虑,找个合适的时间,把马厂长的话转告他,让他得到些慰藉。不过,这次他住院,可能是凶多吉少。他病得很重,连医院的大门也不出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要把马厂长的悔意转告他。
我还没来得及做呢,鲁刚的儿子打电话叫我去医院,说他爹不行了,让我过去看看。
我连忙往医院跑。到了病房,我看见鲁刚正闭着双眼,咬着牙关,躺在病榻上。鲁刚的儿子告诉我,他爹已经两天没睁眼了,医生说,可能挺不过今天晚上。
我俯身到鲁刚的耳边,大声呼唤他。也许是奇迹吧,鲁刚睁开了双眼,对我笑了笑。我不禁悲从中来,鲁刚的笑容,比哭都难看!
鲁刚又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病人在最后的关头,医生总要采取点什么措施的。
我对鲁刚的儿子说了些宽慰的话,看着鲁刚,仿佛看着一盏将要熬尽的油灯。
鲁刚的老伴儿来了,来给鲁刚换衣服了。
鲁刚正在冥冥中离去。我再次趴到鲁刚的耳边,大声地告诉他,我见到了马厂长,马厂长道歉了!
鲁刚又微弱地睁开了双眼,嘴角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
他又闭上了眼睛。
呼吸还有,心跳还有。我退出了病房。
在走廊上,鲁刚的老伴儿告诉我,马厂长来过了,拄着拐,还提着一箱奶!
是吗?马厂长来过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医院这么远,还在山坡上……
鲁刚是当天夜里走的。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马厂长也走了,在鲁刚走后的第三天。令我惊讶的是,吴伟山也走了,在马厂长走后的第二天。
我的老同事,一下子走了三位!
真让我感到命运的奇妙!
我经常把这件事说给熟人们听。熟人们听后都嘻嘻一笑。
这让我感到震动。我们这一辈人,发生了多少故事,生死之间,这么轻松就结束了。
后来,我到陵园去给鲁刚扫墓,很意外地发现,马厂长、吴伟山安葬在他的身边。他们仨的墓地紧连着。(秦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