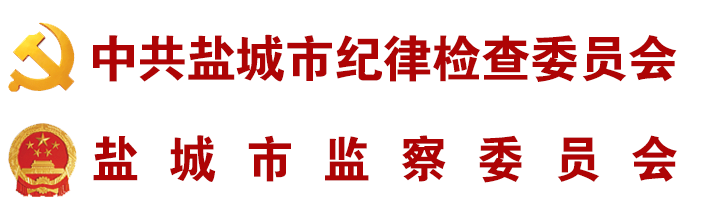小满记忆
提及小满,印象最深的还是孩童时期姥姥家所在村子的“小满物交会”。小满会前夕,我就开始在家里偷偷地翻日历牌,一页一页地数算。小满会当天,无论是否是周末,老师都会让我们放假一天。村子很大,全村将近五千人,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去村里赶会。村子东部的那条街南北将近三里长,自然也是主会场,大街两侧多是卖镰刀、木锹、铁叉、扫帚、草帽等物品的商贩,其次就是卖换季服装的摊点。
小满会那天,一大早,等不及母亲把家务收拾妥当,我就先行跑到姥姥家去赶会。姥姥家是个大家庭,姥姥有七个子女,母亲为姥姥的长女,下面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小满会也是团圆聚会的日子,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比过年都热闹。
每逢小满会的前一天,姥爷就精挑细选准备好集会当天的蔬菜、主食和调料。他有个习惯,做饭不让任何人帮厨。在院子的南墙边,姥爷亲手盘了一个灶台,小满会这天就派上用场,负责做我们一家人的大锅饭。印象最深的就是姥爷炸制的红薯丸子和韭菜丸子,味道香、色泽鲜、口感好。
姥姥乐善好施,每逢小满会总要熬一大锅绿豆小米汤,招呼街上做生意的商贩以及赶会的乡人来家里喝米汤。也有实在过意不去的商贩和乡人执意要给钱,都被姥姥起急动火地拒绝。起初,家人都反对她,可姥姥坚持了三十多年,直到她晚年卧病在床,不能起身。
最惬意的是,小满会也是我借机“敛财”的好机会。由于姨多的缘故,这个姨给三五毛、那个姨给三五毛,一天下来能积攒两三块属于自己的钱,然后拿着这些钱偷偷地跑到集会上,买上一个五分钱的硬邦邦的冰糕,咬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吃个痛快。
每到小满会这天,终于可以在母亲的带领下,到集会上自己做主挑选一双样式、颜色都心仪的塑料凉鞋。等不及母亲把钱给商贩,我就离开摊位,在一旁美得偷乐,唯恐踩到泥土粘上纸屑,与其说是低头看路不如说是低头看鞋。
不能忘记的还有在姥姥家院子里,我和表妹表弟相互追逐嬉闹,玩得不知疲倦,被母亲呵斥、被姨叫停、被姥姥姥爷三番五次地催促吃饭。孩童的喧闹声掩盖了大人们的说话声,欢声笑语回荡在姥姥家院子的每个角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独居的姥姥在小满会的前夕总是托母亲、姨让我们这些外甥、外甥女去赶会。那时我和两个哥哥、表妹、表弟都先后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或是在外地求学。因故,小满会上我们总是聚少离多。有时,只是让姥姥接过母亲或姨的电话,和姥姥说会儿话。
只是,五年前生日那天,我在单位接到舅舅打来的电话,得知姥姥永远离我们而去。
小满时节忆小满,南墙边姥爷盘的灶台被雨水淋毁,姥姥烧香摆放供品的青石香台被灰尘覆盖,曾和舅舅一起拽水的老井被垃圾填埋。花盆杂乱地堆放在屋檐下,干瘪的土里没有一株花草,院子里树上的香椿再也没人采摘。
如今的小满,还有姥爷炸制美味的丸子吗?还有姥姥招呼乡人喝米汤时忙碌的身影吗?至亲的姨,还会给我买冰糕的零花钱吗?母亲还会陪伴我挑选最爱的塑料凉鞋吗?姥姥家还会飘荡我和表妹表弟们追逐嬉闹的欢声笑语吗?
有,这一切都有,这一切都没远走,都被姥姥家街门上那把锈锁,紧紧地锁在了院子里,牢牢地锁在了心底。(纪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