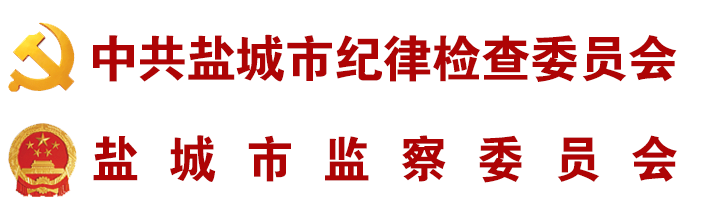遥望家乡
赶牛鞭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看见父亲精心制作一根赶牛鞭。
通常是从宅后砍一棵竹子,斩断削平。
父亲握在手里,时而像将军一样指点,时而像指挥家一样挥洒,时而像武林高手一样舞动。
而在我看来,则像乡村教师手中的教鞭。
一根牛骨头做成的砣,挑选的棉花在手里捻成线,这个简单枯燥的动作,父亲一做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直到把麻线织成细绳在竹竿上捻紧。
父亲蹲在地上上下左右飞舞,炸出一阵阵二踢脚般的响声,惊得树梢上看热闹的群鸟慌乱飞散。
但我从没有见过父亲抽在牛的身上,从来没有。很多时候,赶牛鞭用来捆扎青草,拴牢牛栏,如果天气乍冷,父亲将赶牛鞭扎在腰间,抵御寒冷。
在牛的身后,父亲不停地挥动赶牛鞭在半空中炸响,有时像斥责牛的偷懒,有时又像为勤奋的牛鼓掌,更多的时候像魔鞭,把一天又一天的夕阳甩下西山。
稻草
是苗,绿油油地怀着全村人的念想。
也是草,有一方泥土就长个,有一口水喝就孕穗。
在脱谷机近乎疯狂的打击下,你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果实。
失去稻米的你,被无情地弃之一隅。
但你的价值并没终结。
骄阳将你烘焙成黄金般成色,码成垛,堆成村庄的山峰,整个冬季,那是牛的口粮。
铺在床上,抵御西北风的侵浸。
烧成灰了,是优良的肥料,抛洒在肥力欠缺的旱地,滋养麦苗油菜高粱……这些同门兄弟。
乡下人对你怀有感恩之情,每一个死去的人都睡在稻草上,乘一只草做的筏,赶往天堂……
淘井
那年大旱,老天干打雷,不下雨。
村里唯一的水井,像倒竖的烟囱,旱得冒烟。
淘井的那一天,我提心吊胆:我亲眼看见父亲,从家门走近老井,脱下鞋,卷起裤角,光着脚,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我俯在井栏上,望着深不可测的井下,只听见“咚咚”沉闷的声响,像是父亲心跳的回音。
我无比恐惧,担心父亲深潜于井中,与井底之蛙为伴。
我充满期盼,等待父亲如神话中的神仙,扶摇而上。
一只轱辘,吱吱呀呀把潮湿的沙土摇上来。我连忙扑过去,捧起水淋淋的黑土,深一口浅一口嗅着父亲的味道。
那天,漫长如年。
一阵欢呼声中,父亲如凯旋的英雄与久违的井水一起溢出井沿。
很多年,我喝着井水,有一股浓浓的脚臭味。
但村里男女老少异口同声说:“甜!”(许泽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