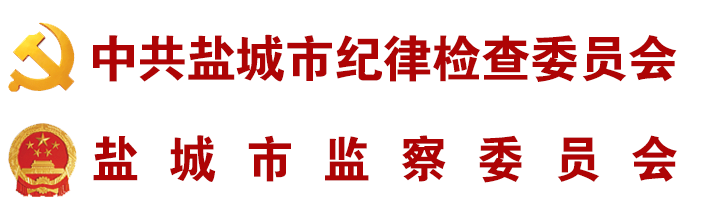芦花两岸雪(散文)
湖边,生长着无边边际的芦苇。
芦苇,一丛连着一丛,一片连着一片。苇叶是温暖的黄,芦花是轻柔的白。太阳洒下来,一群水鸟扑棱翅膀从芦苇丛飞向天空,整个湿地活泛起一种生命的明亮。
风起,芦浪翻涌,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饱满的力量。没有谁可以驾驭风的走向,芦花的命运注定“随风而逝”。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不问西东,顺天适性,该努力生长的时候就努力生长,该抽穗扬花的时候就抽穗扬花,该零落成泥的时候就零落成泥,足够了。何况,每一个逝处,其实不都是生命重新开始的地方吗?看着吧,只要根下有一点儿湿土,一到春天,定能“蹭蹭蹭”地长出一片新绿。这么多的芦苇,每年开了谢谢了开,多像一茬茬青春的孩子。
夕阳敛约光线时,有鸟归巢,却始终都没听到芦苇的声响。这是一种不出声响的植物。世间的寂寞它能忍受,异语的聒噪它能忍受,风雨的磨砺它一直都在默默忍受,永远是那般细腻修长。当遭遇外力不得不委婉成一根弧线时,它依然可以依赖内心的韧性挺拔如初,于是就有了玉树临风的清洁风骨。
一朵芦花落在我的袖子上,毛茸茸的。又一朵芦花亲吻我的脸颊,一些往事漫过记忆,从岁月深处涌上心头,世间跋山涉水的悲壮以及悲壮之后难以言喻的柔情交织在一起。
我假装看不见芦苇。我只看到又圆又大的夕阳。远山那一片云以最快的速度苏醒。小时候的世界,开始重新热闹起来。印象中母亲是不喜欢夕阳的,她的眼里只有那些芦苇。对芦苇看不够的母亲,每一次,都会把最沉默的那一支带回家。“最沉默”是我的说法,我觉得它把头垂得最低,最想亲吻沉默的大地。
带回家的芦苇,一天接一枝地,全被母亲安插进了那只泛着温润光泽的大瓷瓶里。那是父亲出差景德镇时,特意买来送给母亲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一两个月回一次家,回家总带给母亲礼物。
插进瓷瓶的芦苇再不是水的骨头了,它仿佛会变魔法,不仅是把它自己、连带着把整个世界都变得无比蓬松柔软。看一眼芦苇,再看一眼母亲,我似乎一下就跌进了梦境。
其实我也是无比想念父亲的。思念快要把胸膛撑破的时候,芦苇也把瓷瓶插满了。我慢慢发现一个秘密:芦苇把瓷瓶插满时,父亲一准回家了。这个秘密使我的心“怦怦怦”地响过好几回,每次母亲带我们去渠首边折芦苇的时候,我就跑得远远的,我怕母亲窥破这个秘密。因为当秘密不是秘密,日子便无所期待了。无所期待的日子未免也太不好玩了些。
父亲把我和弟弟挨个高高举起,清脆的笑声在他的头顶打着转,向屋瓦向天宇漫散。回家的父亲把母亲紧紧搂在怀里,之后,帮着母亲把瓷瓶里的芦苇一枝一枝取出来,扎成一把结实的扫帚,扫去人间万般愁。尘障总是越扫越少,路也会越走越宽。几年之后,父亲买了房子,将留守乡间的母亲及我们接了去。那一刻,瓷瓶最空,母亲的心最满。那一刻,因为母亲脸上的熨帖,我无比欢喜起故乡水渠旁的芦苇。
与父亲团聚了的母亲,执意让瓷瓶空着。
母亲将瓷瓶送给我,作为嫁妆的一部分。母亲的心意,我懂,所谓岁月静好,莫过于心被爱填满而瓷瓶空着。
多年以后,当我行走在这条水上公路时,我在想,该如何向母亲形容眼前所见的芦苇?不是一枝两枝,不是一簇两簇,是铺天盖野,是辽阔无边。我又该如何向母亲启齿——她的女儿,一个年届不惑的女人,正被不可知的远方所吸引,要打破现世的安稳、离开熟悉的县城去省城工作。一切从头来过,她其实也很担心也会害怕,带给爱人、孩子的,究竟是幸福还是忧愁?
芦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生活是流动的河流,唯流动才能生生不息,我终究还是迈出了去往省城的那一步。我、婆婆、孩子在省城,爱人、父母在县城。空着的瓷瓶,在离开家时特别醒目,像生活被撕裂的那部分,使人不忍直视。我便在摆放瓷瓶的正上方墙壁上挂了一幅风卷芦苇的图画。爱人端详画许久,告诉我:“放心吧,所有的春天都是从芦苇开始绿的。”这句话,使我流了许多幸福的泪。我想到了另一幅画,波提切利的《春》:水星神指引生命最珍贵的美、春、爱向无终的大路上迈步前进,虽然生命的仇敌——西风——在后面追捕,他们仍旧勇往直前。有人说此画可叫《生的胜利》!
芦苇所经历的,我必将经历。当一切慢慢走上正轨,母亲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放心吧,母亲,漫卷芦苇的长风从来不是困厄,它应该是梦想。浩荡长风,自由勇敢,无惧无畏。大凡被长风培育过的事物,都跌宕而柔韧、蓬勃而绵远。(罗张琴)